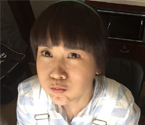来源:生活报
原标题:哈尔滨第210位遗体志愿捐献者,将用余下时光做一件大事……他要输得精彩
肝癌晚期的冰城“老文青”王伟宏志愿捐献遗体
连载“生命日记”记录“最后的时光”
......
“人生已是残局,我想输得精彩”
57岁的哈尔滨人王伟宏,静静地站在哈医大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的办公室里,看着女儿在捐献志愿书的“遗体”选项上,替他画下了人生中最庄重的一个“√”。
没有沉重的叹息和悲伤的眼泪,一切平静得就像医大校园里的林间小路。11月23日这天,王伟宏成为了哈尔滨市第210位志愿捐献遗体的人。
王伟宏是一名肝癌晚期病人,已经发生骨转移。半个多月前,他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连载“生命日记”,记录自己“最后的时光”。
他在公众号里写道:“无论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,我都会认真地说,我没活够,我留恋这个世界……捐献遗体,就像是我悄悄地在这世界上安放了一枚棋子,他代替我继续参与这个世界,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,也是我生命的无形延伸。”
筒子楼里的时髦来客
12月6日,气温骤降。在香坊区建成早市旁的一栋黄色筒子楼里,王伟宏站在二楼的露天走廊里,笑呵呵地向记者招手。
他穿着一件时髦的蓝色高领毛衣,下巴上留着一撮灰白色小胡儿,文艺儒雅的气质与这栋破败的老楼不太相称。王伟宏原本不属于这里,去年年初在北京体检时,他被发现肝部有恶性肿瘤。8月做完手术后,发生了骨转移。今年7月,他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北漂生活,辞别京城文案策划圈的老友们,回到家乡哈尔滨治病。由于自家住五楼、爬楼困难,他在家附近租了个20平米的小屋。

如果光看外表,王伟宏不太像癌症晚期的病人,他神采奕奕、语速飞快,特别是聊起当年做过的那些较为轰动的文案时,兴奋而又骄傲。只是,突如其来的疼痛,有时会让他嘴角微微颤动,但很快又恢复平和。
“我现在除了睡觉,其余时间一直站着,一旦坐下,站起时脊椎巨疼。”王伟宏绕着自己的躯干画了个圈,平静地说:“医生说了,除了大脑和四肢,癌细胞已经占领了我所有的骨头。”
他隔周要去肿瘤医院和哈医大二院做例行检查,配合临床试验小组的治疗。为了避免外力伤害,出门前要先将护具绑在胸前,医生曾告诫他,一旦出现外力撞击或震荡,很可能会高位截瘫。每次打车去医院时,他都小心翼翼地叮嘱司机:“慢慢开,尽量不要急刹车”。
被“刷新”的生死观
对王伟宏而言,癌症就是他加速人生中的一次“急刹车”。他16岁接父亲的班,在燃料公司当宣传干事,因文笔出众被借调过市作协,中间当过一年记者,后来又去北京的广告公司干策划,升为策划总监,让他引以为傲的是,曾经靠着一篇优秀的文案卖掉过1000多万元的月饼……
在火热的80年代,他组建过诗社,写过不少类似于“白昼是我们的身体/夜晚是我们的灵魂”这样的句子。一个月前,他们诗社的纪念集完稿成书,回味着那些青春记忆,他唏嘘不已。当年,他还热衷哲学,面对人世的种种怪象,愤世嫉俗地说:“关于你们人类的事儿,我再也不想了。”

年轻时,王伟宏跟好友探讨过死亡,他希望自己能死得悄无声息,朋友则渴望死得体面安详。2006年10月,那位朋友突发心梗去世了。王伟宏赶回哈尔滨,在太平间里见了朋友最后一面,他清楚地记得:“那张脸上写满了不情愿,一点儿也不体面。”看到他的家人们因为一些细节起争执,从各地赶来的朋友则在尽情地缅怀青春岁月,王伟宏突然意识到:“死亡这件事儿一经发生,就与死者再无关系了。”
五年前,一个亲戚的离世,再次“刷新”了王伟宏的生死观。他看见大家为逝者买各类祭祀用品,亲眼目睹上万元的实木棺材被付之一炬,他深深地觉得:死亡的本质在这里被扭曲着,祭奠的形式在这里被曲解了。
回到家,他跟女儿说:“我决定将来捐献我的遗体,简化所有的程序,取消所有的开销。”
有张床叫“阳光浴场”
王伟宏曾经看过一部外国电影,已经想不起名字,但对里面的一句台词印象深刻:“可怕的不是灾难本身,而是灾难带来的恐慌。”
生病后,他努力让自己过得自在、舒心,每天绑上护具逛早市,为了锻炼身体,也为了“沾沾人气儿”,他听民歌、弹吉他,看开心麻花的电影,眉飞色舞地模仿其中的搞笑桥段。

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,是午后躺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晒肚皮,他管那张床叫“阳光浴场”,并讶异于“以前怎么没发现,原来晒太阳这么舒服。”他为每寸被冬天偷走的阳光“斤斤计较”,最近正跟太阳高度角闹别扭,为那些越过床单浪费在地板上的暖阳深深惋惜。对他而言,或许一万个美丽的未来,都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。
这些细小的欢喜,终究还是难以冲淡巨大的痛苦。“癌痛会消磨人的意志,每次发作都如同一场‘严刑拷打’。”王伟宏感慨道,有时他几近崩溃地躺在床上,对着空气呼喊:“我招了!”“我全都招!”然而,病魔似乎并不需要他回答什么,只是一味地折磨人。
想给自己办个生前葬礼
北漂二十多年,王伟宏一个人过得很潇洒。生病后,他的情感变得有些脆弱,甚至有些粘人,有时变着法儿地找借口让女儿来看他,“我俩每天晚上一起吃饭,我就是想多跟她待一会儿。”有一回,他躺在“阳光浴场”上,听女儿用手机放了霍尊唱的《小草》,差点儿泪奔。
明年3月,王伟宏想在58岁生日时给自己办个生前葬礼,他对悼词里“不幸离世”这样的套话颇为不屑,甚至有点儿恼火:“死亡怎么就不幸了?!人生几十年,从生到死,应该是有幸过了一辈子才对。”他要亲自监督,给自己办个与众不同的葬礼。

这个有点儿任性的“独行侠”,最近也开始“关心人类”了,他写文章告诫病友:“很多人因为得了癌症乱了阵脚,寄希望于各种偏方,越是大病越不能乱投医,因为没有多少可以修正的机会。”
跟记者聊天时,王伟宏多次提到“价值”这个词儿,他还是觉得“这辈子得留下点儿什么”,除了写“生命日记”,他还跟人合作写书,并打算将北京的文案沙龙移植到哈尔滨,每周演讲一个主题,将自己的毕生功力倾囊相授……
王伟宏痴迷象棋,年轻时曾因为下棋误过很多事儿甚至丢过工作,在他看来,人生跟下棋不一样,一盘棋输了可以推倒重来,可是人生只有一次,“我的人生已经进入残局了,即使是输,我也要输得精彩”。说这话时,他表情认真而又严肃。
文字: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摄影:生活报记者 张宇驰